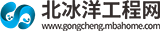不经意间,河边的垂柳醒了。
柳树稀疏的线条在风中摇曳,如同一幅淡淡的水墨画。柳条上已经长出嫩芽,这些毛茸茸的翠色,恰似小蝴蝶扇着翅膀。一路走过去,柳树婀娜的姿态开始变得遥远、变得缥缈、变得诗意。恍惚中,仿佛穿越时空,走进了古代,走向灞桥、隋堤,走向长亭外、古道边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,这是志南的乐趣;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”,这是高鼎的闲适;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”,这是王维的不舍;“无情最是台城柳,依旧烟笼十里堤”,这是韦庄的慨叹;“一树春风千万枝,嫩于金色软于丝”,这是白居易的柔情……在古人眼里,柔软的柳枝是一种托付,传递着人们的喜悦和哀怨。忽然想起北方的一位朋友。前几天,他在朋友圈晒图,还是一片冰天雪地;现在,如果我给他快递一段缀满芽苞的柳枝,告诉他春的消息,他会不会与我一样高兴?小城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,该是多么风雅的事情啊。
柳树不仅是信使,也是一种壮美之树。记得有一年去新疆,在哈密河的湿地公园听到了一个故事,与柳树有关、与左宗棠有关。光绪元年,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,率军进入新疆平叛。河西地区“赤地如剥,秃山千里,黄沙飞扬”的大漠景象令左宗棠忧心如焚,他命令军士随身携带树苗,在沿途路边、宜林地带、近城道旁栽种,并要求每棵树都挂上栽种人的姓名,每隔一段距离还要挂盏灯笼,以免过往骡马车辆撞坏树木。在左宗棠的督促下,军卒一路走一路栽,竟在甘肃通往天山南北的交通驿道旁形成了“连绵数千里,绿如帷幄”的塞外奇观。这些柳树就是赫赫有名的“左公柳”,如今从陇东到玉门仍然随处可见杨柳依依的景象。左宗棠的部下杨昌浚写道:“大将筹边尚未还,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,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既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,也是对左宗棠植树造林的歌颂。
或许很少有人知道,柳树还是一种音乐之树。大学毕业前夕,我和几个同学去通许县一所中学实习。学校坐落在一片田野上,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,几间破旧的青砖瓦房就是教室,三五棵高大的柳树分列在围墙外面。这个地方很偏僻,学生衣着朴素,学习却很勤奋,他们早晨从周边的村庄匆匆赶到学校,中午不回家,午餐是在学校伙房里买的两个馒头外加一碗蒸馍水。看到我们到来,学生眼中写满了惊喜和亢奋,上课时他们听得很专注,课间也围着我们叽叽喳喳问各种各样的问题。
当时正值初春,几个男孩遇到在田间散步的我,变戏法一般拿出几根泛青的柳条,说是要做一种叫“鸣鸣儿”的哨子。他们用随身携带的小刀从柳枝上切下一小段,捏住两头向相反方向轻轻拧动。等柳皮与柳骨全部分离,就用嘴咬住一端,缓缓抽出光滑的柳骨,手中便有了一截软软的柳皮管。然后,把柳皮的一端捏扁,用小刀刮去外皮,直至露出鹅黄的内皮,“鸣鸣儿”就做成了。孩子把“鸣鸣儿”放在嘴里试吹,或急促、或清脆、或低沉,此起彼伏,呜呜有声。我们坐在田埂上,说着,笑着,吹奏着。身后是麦田,麦田的上方是蓝蓝的天空,天空中浮着几朵白云,掠过几只飞鸟。“鸣鸣儿”虽然是一种简易乐器,我们却用它吹响了春天,在大自然中享受到一种质朴而纯净的快乐。
当初我们做的“鸣鸣儿”雅名叫“柳笛”,30多年过去,柳树的枝条青了又黄、黄了又青,却不知曾经吹响柳笛的少年去了哪里。而今,春天又来了,看到柳树,不由得想起了往事,似乎又听见柳笛声声,划破了时光的静寂。
(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漯河市漯河实验高中)
《中国教师报》2023年03月01日第16版
作者:王 剑